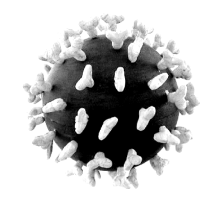作者简介:朱晶,女,1984年生,学士,技师,主要从事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工作。
通讯作者:潘柏申,联系电话:021-640419902376。
嗜酒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 可导致无法逆转的心理和生理损伤, 也会造成家庭和社会问题。例如嗜酒的孕妇可能使孩子患有胎儿乙醇综合征, 每600个新生儿中有1个将因此智力发育迟缓[1]。因而正确判断饮酒状态在临床医学、法医学和司法等不同领域都有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检测方法包括体格检查、调查询问和一些临床生化标志物。后者虽然相对比较客观, 但对于判断饮酒状态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欠佳。近年来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了一些新的饮酒标志物, 如乙醛蛋白加合物、脂肪酸乙酯、5-羟色醇等。其中糖缺失性转铁蛋白(carbohydrate-deficient trans-ferrin, CDT)无疑是目前最受关注的一项新标志物。自1978年被发现后, CDT迅速成为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焦点。无数研究结果证明CDT与饮酒状态具有紧密的相关性, 是目前敏感性和特异性最佳的独立的标志物。2001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CDT作为一项用于评估饮酒状况的标志物应用于临床。CDT的发现和应用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既可有效评估饮酒状态, 也为酒精相关疾病的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
早在1976年, Stibler等[2]在运用等电聚焦电泳法研究神经疾病患者的脑脊液和血清蛋白时, 发现了酒精性小脑退化患者的脑脊液和血清中都存在异常微观不均一性的转铁蛋白, 其中有些蛋白组分的等电点(pI)为5.7。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 这种pI为5.7的转铁蛋白多见于嗜酒者的血清中, 在禁酒一段时间后便会消失, 因此推断此类转铁蛋白对判断饮酒状态具有较好的特异性, CDT也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热潮。随后很多较早期的研究都得出CDT与饮酒状态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 敏感性和特异性都很好。但是这些早期研究由于方法学本身的限制而遇到了一些阻碍。当时的方法是在等电点聚焦后再进行免疫学检测从而得到CDT定量结果, 对于临床常规检测而言实属繁琐、耗时。之后随着方法学的不断发展革新, 检测方法运用了离子交换层析技术、层析聚焦技术、联合放射免疫方法以及最新应用的质谱方法等, 这些技术大大推进了CDT在更多人群中的临床研究。
转铁蛋白主要由肝脏细胞合成, 相对分子质量为795 000。含有3部分结构域, 即1条由679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链和2条糖链, 2个糖链结合位点分别位于肽链的413号位和611号位[3], 可结合不同的糖链分子。因此转铁蛋白的结构在非病理情况下也会呈现一定的多样性, 其本身并非是一种结构均一的分子, 而是具有独特的异质性。
转铁蛋白肽链上的2个糖链结合位点分别可结合2支、3支或4支的糖链, 每支糖链末端为一个带有负电荷的唾液酸分子。若转铁蛋白未结合糖链, 则为无唾液酸转铁蛋白亚型。若糖链结合位点分别结合了2支、3支或4支的糖链, 则可呈现单唾液酸至八唾液酸的转铁蛋白亚型。正常人血清中不同转铁蛋白亚型所占转铁蛋白总量的比例也各不相同, 含量最多的是四唾液酸分子亚型, 见图1, 占总量的64%84%; 五唾液酸分子亚型占12%18%; 三唾液酸分子亚型占4.5%9%; 双唾液酸分子亚型< 2.5%; 六唾液酸分子亚型为1%3%; 七唾液酸分子亚型< 1.5%, 几乎不含无唾液酸或单唾液酸分子亚型[4]。由于唾液酸带有负电荷, 含有不同个数唾液酸分子的转铁蛋白pI从5.5至5.9不等。在电泳检测中, 转铁蛋白不同亚型的迁移率不同因而得以区分, 这也是检测CDT的基础原理。
饮酒后体内转铁蛋白所含的唾液酸分子减少, 使三唾液酸、双唾液酸、单唾液酸和无唾液酸的转铁蛋白亚型水平升高。有研究表明实际上转铁蛋白缺失的不仅仅是唾液酸, 也可能是整条糖链的缺失, 即转铁蛋白糖化程度的降低。另有研究表明占CDT主体部分的无唾液酸转铁蛋白是由于缺失2条糖链所致, 而双唾液酸转铁蛋白则是缺失1条糖链所致[5]。
Stibler等[2]首次报道了于嗜酒者的脑脊液和血清中存在pI为5.7的转铁蛋白亚型。此类亚型含有的唾液酸较少, 肽链的糖化程度降低, 其含量增高多见于嗜酒者体内, 并在禁酒一段时间后又会消失, 半衰期约14 d。这些亚型包括无唾液酸转铁蛋白、单唾液酸转铁蛋白和双唾液酸转铁蛋白, 目前将此类并称为CDT。
非饮酒状态下人体内最为常见的是含有4个唾液酸的转铁蛋白亚型, 为何CDT的定义中并未包含三唾液酸转铁蛋白?饮酒能否导致三唾液酸转铁蛋白水平升高?三唾液酸转铁蛋白能否提高饮酒的诊断效率?答案是否定的。三唾液酸亚型是转铁蛋白糖链末端的一个唾液酸分子被其他不带电荷的糖分子替换(如半乳糖或甘露糖分子), 并无糖链的缺失。Dibbelt[6]于2000年时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证实了三唾液酸亚型与饮酒状态没有相关性。随后有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观点, 结果表明若将此亚型纳入CDT, 则会降低饮酒的诊断特异性[7]。因此三唾液酸转铁蛋白亚型并未列入CDT的范畴。无唾液酸和双唾液酸亚型分别是转铁蛋白缺失2条和1条糖链后的产物, 对于酒精的特异性更高。
在不饮酒的正常人血清中几乎检测不出无唾液酸和单唾液酸转铁蛋白亚型。而在饮酒者血清中存在无唾液酸亚型, 并且双唾液酸亚型水平也大幅增加。因而虽然理论上CDT的定义包含了单唾液酸亚型, 但其与饮酒状态的相关性并不如其他2种亚型。也有人提出CDT中的无唾液酸转铁蛋白是与饮酒状态最为相关的亚型。甚至有学者提出仅检测无唾液酸亚型更优于检测所有CDT亚型。如Arndt[4]认为用毛细管电泳检测无唾液酸亚型不仅可判断禁酒者和饮酒者, 还可判断适量饮酒和过量饮酒。虽然仅检测无唾液酸亚型对于饮酒状态有很好的特异性, 但大大降低了其检测的敏感性。因而目前临床上应用的大部分检测试剂是同时检测无唾液酸和双唾液酸亚型, 以同时确保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转铁蛋白被释放入血浆前会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转录后蛋白修饰。在粗面内质网中, 多肽链会与富含甘露糖的寡糖结合, 最终在高尔基体中完成整个糖化过程。糖化对于细胞内和细胞外的信号介导、分割迁移、免疫抗原性、蛋白质可溶性、酶活性和生物半衰期等都起着重要作用。糖化的过程包含在糖蛋白末端连续附加N-乙酰氨基葡萄糖、半乳糖和唾液酸, 其中至少有5种糖转移酶参与, 主要由唾液酸转移酶调节。
自1976年发现以来, 酒精诱导CDT水平增加的病理机制并未完全了解。Sillanaukee等[8]总结了酒精诱导的糖蛋白代谢变化是多步骤的过程, 涉及了蛋白转运和酶的活性。酒精及其代谢产物能抑制肝细胞合成转铁蛋白和磷酸甘露糖转移酶的活性, 因而CDT水平升高。也有学者认为酒精及其代谢产物乙醇会影响高尔基体内糖链的合成; Stibler等[9]检测到饮酒者血清内半乳糖基转移酶和N-乙酰葡萄糖氨基转移酶活性降低, 使转铁蛋白糖化程度降低。
尽管有大量研究试图解释饮酒为何能产生CDT, 但目前产生的具体机制仍不明确, 但确定其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而是由多种酶类参与、多步骤的过程。如今发现在长期饮酒后, 肝细胞膜表面唾液酸转移酶活性降低, 而血浆中唾液酸水平升高, 因而唾液酸无法进入肝细胞进行糖链合成, 可能是饮酒后产生CDT的机制。
在CDT被广泛应用之前, 传统的判断饮酒状态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包括γ -谷氨酰转移酶(GG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平均红细胞体积(MCV), 但这些项目都有共同的三大缺点。第一, 虽然这些指标都对肝脏疾病有较好的特异性, 但却无法区分不同的病因, 对酒精没有特异性; 第二, 在饮酒导致肝脏损伤之前, 这些指标的水平没有变化; 第三, 这3个标志物的半衰期较长, 无法及时反映饮酒状况的变化。毫无疑问, CDT是迄今为止对判断饮酒状况最为理想的标志物。目前国外CDT主要在临床上运用于嗜酒者解毒治疗的监测, 也被推荐用于糖缺失糖蛋白综合征(CDG)的辅助诊断、判断急性胰腺炎的发病是否与饮酒状态相关、无意识的颅内出血筛查等, 尤其对于精神治疗或初级医疗部门患者、创伤和术前患者, 检测CDT可预测急性戒酒综合征的风险[10]。另有研究发现当酒精性肝病患者存在肝纤维化或脂肪肝时, CDT与其他生化指标(如GGT、AST/ALT比值)联合应用可进一步提高FibroTest和SteatoTest的准确性[11]。提示CDT还可辅助鉴别酒精性肝病是否同时存在肝纤维化或脂肪肝。此外CDT还可用于鉴别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炎。由于缺乏准确诊断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症状或生化标志物, 因而在诊断时若能有效排除酒精性肝炎是非常必要的。有研究表明, 虽然AST、AST/ALT比值、GGT、MCV和CDT在酒精性肝炎患者中均有所升高, 但仅有CDT在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中的水平低于Cut-off值[12]。说明CDT能有效鉴别酒精性和非酒精性肝病, 对非酒精性脂肪肝有很高的排除诊断价值。CDT升高与下降还可用于判断遗传性果糖耐受和半乳糖血症的饮食治疗疗效, 这是CDT比较新的应用领域。果糖血症和半乳糖血症患者体内都存在蛋白糖化的异常, 治疗前这些患者的CDT水平均升高, 在有效治疗后CDT水平将下降至正常水平。因而CDT水平的变化对于果糖血症和半乳糖血症的诊断和疗效评价都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尤其在治疗时建议定期检测以有效监测治疗效果[13]。
但在临床实际应用中, 对于CDT的结果解释也存在几方面的争议, 如CDT是否应与GGT联合应用?CDT与饮酒量或饮酒方式间有何关系?CDT反映的是长期饮酒还是短期饮酒?是中度饮酒还是重度过量饮酒?是否能提示饮酒的风险?能否辅助诊断酒精性肝病?真正恰到好处地应用CDT, 使其最大程度的发挥临床应用价值就必须解开这些疑问, 但有些疑问目前还没有绝对的答案。
1.CDT与饮酒量通常认为每日摄入5080 g酒精持续至少1周后, CDT水平将升高。也有文献更确切地指出平均每天摄入46倍的标准饮酒量(1014 g酒精/d)至少2周, CDT水平会增高[14]。而禁酒一段时间后其水平又将下降至正常水平, CDT半衰期约为14 d。但根据CDT能否对饮酒量做出推断目前还存在疑问, 尤其对轻度饮酒的人群。甚至有文献指出CDT对女性饮酒者的特异性不如男性。基于目前大量发表的研究, 人们对于CDT水平升高与摄入酒精5080 g/d持续1周之间的相关性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但对于CDT与每日饮酒量控制在推荐水平内, 即2040 g/d之间的相关性还存在争论。经过对1 694名对象的研究后发现, 对于男性而言, 最佳的诊断特异性是对最近30 d每天饮酒60 g的人群。有研究表明, CDT与酒精摄入量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表现于超过40 g/d酒精摄入量, 相当于中度至重度饮酒人群, 但对于相对轻度的饮酒人群, 其CDT水平可能处于Cut-off值以下[15]。
2.CDT与长期饮酒CDT与短期内饮酒的相关性已很明确, 但其与长期或慢性的饮酒是否也相关?这一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答案, 可能取决于饮酒的具体方式。有研究表明, 长期的少量的饮酒可使CDT水平增高, 而短期内大量饮酒并不会使CDT水平上升。由于医学伦理方面的限制, 长期饮酒与CDT间的研究很难开展。CDT目前暂不用于长期饮酒的诊断主要是因为其诊断敏感性较低, 限制了CDT这方面的临床应用。Stibler[16]曾报道CDT对于慢性饮酒的敏感性达到90%以上, 使人们对于CDT给予了厚望。但在随后的其他研究中发现, CDT对于慢性饮酒并没有如此理想的诊断敏感性, 根据不同的饮酒方式、每日饮酒量对女性诊断的敏感性为30%50%, 对男性诊断的敏感性为50%70%[4], 无法满足临床检测需求。
3.CDT与GGT的联合应用在CDT被广泛应用之前, GGT曾是慢性饮酒最常用的标志物。与GGT相比, CDT有着更好的特异性(GGT为75%、CDT为92%), 并且在病理情况下也依然表现了良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14]。人们也不禁猜想是否将两者结合能更好地对饮酒状态做出判断呢?因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表了很多比较CDT和GGT, 或将两者联合应用后的诊断特异性和敏感性的文章。根据对于不同性别、年龄、饮酒量和方式, 不同疾病人群的研究, 从这些大量研究数据中可以得出GGT与CDT的绝对值或百分比结果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对于慢性饮酒方式而言, GGT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而CDT拥有更好的特异性。因而很多学者也建议将两者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性能。Sillanaukee等[8]发表了一篇关于6项对于饮酒者研究的meta分析, 总结了CDT、GGT、AST、ALT和MCV对于饮酒状态诊断的特异性, 指出将CDT和GGT联合应用是最佳检测组合。相同的观点也被Chen等[17]和Imbert-Bismut等[18]的研究证实。
4.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比值在运用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比值之前, 人们曾用pI为5.7的亚型与pI为5.4的亚型比值(即双唾液酸转铁蛋白与四唾液酸转铁蛋白的比值)来减少转铁蛋白水平对于CDT的影响。但由于操作过于繁琐耗时, 因而没有在临床上广泛应用。随后人们想到将CDT与转铁蛋白总量进行比值计算来解决这一问题[19]。与CDT的绝对定量水平相比, 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比值对于饮酒状态的诊断特异性更高, 尤其是对于转铁蛋白总量增高的人群而言(如缺铁性贫血患者), 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比值能更好的规避转铁蛋白的干扰作用[20]。但对于转铁蛋白总量下降的人群(如急性或慢性感染者、血色素沉着病、肾病综合症患者), 即使运用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比值也无法改善诊断特异性, 仍会产生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20]。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比值的检测总误差包含了转铁蛋白和CDT检测误差之和, 因而比仅检测CDT绝对值结果的总误差大。因此在进行结果解释时还需考虑这一问题, 尤其对于处于边缘线附近的结果更应谨慎。
CDT不仅可用于重度饮酒者的治疗监测、酒驾监测等司法领域, 还可用于严禁饮酒职业的入职检查。因而若CDT检测结果不准确可能导致失去工作或无法取得驾照, 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所以CDT不同检测方法的性能评价一直以来倍受关注。由于转铁蛋白本身存在着微观结构的差异性, CDT和非CDT亚型结构之间的差异仅体现为结合的糖链差异, 而且CDT的含量很低(健康对照组人群< 2.5%2.7%)[21]。这些特质无疑对CDT检测方法的分离度、敏感性和特异性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由于目前的技术无法获得针对CDT的特异性反应或特异性抗体, 因而目前实验室常规检测方法是基于色谱法(如离子交换)或电泳法(如等电点聚焦法), 即根据CDT和非CDT亚型pI的差异将CDT进行区分。因转铁蛋白结合不同数量的铁离子也会影响其pI, 为了避免CDT和非CDT由于铁离子差异而具有相同的pI使检测结果偏高, 在检测前将血清标本进行铁饱和, 统一转铁蛋白的铁负荷, 随后再进行色谱或电泳检测。
1.电泳法等电聚焦电泳法有很高的分离度。在具有pH梯度的凝胶上根据不同亚型pI不同将其分离, 在免疫固定和染色步骤之后可见各类转铁蛋白亚型的条带, 最后进行密度计量得到CDT结果。根据定标曲线, 这种方法可得到CDT的绝对浓度。由于等电聚焦电泳法具有很高的分离度, 还可根据条带的不同直接判断出转铁蛋白的基因突变。除了等电聚焦电泳法, CDT还可运用毛细管电泳和毛细管区域电泳法检测, 但分析性能不及等电聚焦电泳法。虽然等电聚焦电泳法有很好的分离性能, 但由于其是根据条带密度进行定量, 因而这种方法无法避免在准确性和精密度方面存在缺陷, 所以逐渐被具有更高定量效能的方法所替代, 如HPLC或毛细管区带电泳等。鉴于等电聚焦电泳法分离性能理想, 也被推荐用于CDG的诊断[4]。有研究证实CDT检测的毛细管电泳法目前已拥有了良好的非精密度、可靠的线性范围, 并且与参考方法HPLC间具有良好的可比性[22]。
2.色谱法在1986年Stibler首次建立了离子交换微柱层析联合免疫检测的方法。色谱法检测CDT敏感性和分离性不及等电聚焦电泳法, 离子交换色谱法检测后再运用免疫法也无法检测出转铁蛋白突变。虽有文献报道HPLC可检测出转铁蛋白突变[23], 但等电聚焦电泳法在检测和判断转铁蛋白突变表现型方面还是优于HPLC, 前者能更好地分离不同pI的亚型。有文献报道, 在英国, 当CDT用于交通医学领域时, 仅使用HPLC作为惟一标准, CDT其他方法的检测结果并不予认可[24]。
3.免疫法免疫法也是由Stibler于1986年首次建立的。由于缺少CDT特异性抗体, 免疫法需要通过离子交换微柱将CDT亚型从血清中分离, 随后加入抗人转铁蛋白血清进行定量检测。这种将色谱法和免疫法联合的检测方法很快得到发展, 并推出了多种商售试剂, 由于其操作简便在实验室被广泛应用。其检测性能也被3项多中心联合研究所证实[25]。但由于缺乏CDT特异性抗体, 此方法的特异性还是依靠色谱层析的分离程度, 而后者往往受检测环境、人员操作的影响。因而也有不少文献指出免疫法的不准确性[26], 尤其是无法将三唾液酸转铁蛋白亚型与CDT分离, 大大影响了检测性能。此外转铁蛋白突变也将干扰免疫法。当转铁蛋白肽链氨基酸发生替换, 会改变转铁蛋白分子的电荷数。迄今为止共发现了38种转铁蛋白突变类型, 根据电泳迁移率分为common型(C型)、阳极型(B型)和阴极型(D型)。有文献指出C型突变由于对于转铁蛋白电荷数影响较小, 对其检测无干扰作用; 而BC或CD型杂合子会干扰免疫检测法, 分别会使结果偏低和偏高[27]。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当CDT用于司法或行政诊断时, 免疫法只能作为初筛试验, 随后运用HPLC或毛细管区带电泳进行确认。2005年, Dade Behring公司推出了一款新的CDT免疫检测系统, 也是目前惟一的一套运用了针对唾液酸分子缺失后暴露表位的抗体的检测系统。标本无需进行铁饱和预处理, 也不用先进行离子交换层析再检测, 自动化程度较高, 同时也不受转铁蛋白突变B或D亚型的干扰, 从而将CDT检测技术跨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由于CDT是一组结构不均一的转铁蛋白亚型, 目前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的表达形式也有不同, 有些是以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百分比形式表达, 有些则以CDT绝对值的形式表示。有些方法仅检测CDT特定的亚型(如双唾液酸转铁蛋白), 有些则检测CDT所有亚型。不同方法间特异性、敏感性、Cut-off值的设定也都不尽相同, 检测结果可比性较差, 往往在实际运用中不但使临床感到困惑, 也对CDT检测的标准化提出了挑战。为了建立一套参考系统、参考物质和参考方法, 推动CDT检测结果的标准化和一致性, 国际临床化学学会(IFCC)于2005年专门成立了CDT标准化工作组(WG-CDT), 于美国和欧洲共设立5家参考实验室, 并扩展建立起涉及全球66个医学实验室的网络, 覆盖了目前所有的CDT常规检测方法。工作组选择HPLC作为候选参考方法, 检测评估候选参考物质, 旨在使不同方法检测结果间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并统一Cut-off值。从2010年该工作组发表的第2份报告来看[28], 目前的候选参考方法和参考物质已拥有良好的检测性能和重现性, 可用于给定标品和质控品定值。因而一套完整的CDT参考系统即将呼之欲出。
为何工作组将HPLC作为候选的参考方法呢?目前CDT常规检测方法有HPLC、毛细管电泳法和免疫法。间接检测CDT的免疫检测法存在无法避免的技术缺陷, 很多研究都认为其检测性能欠佳。目前市场上只有Siemens N Latex CDT 系统是直接检测CDT的免疫方法。该系统所运用的特异性抗体直接针对糖链缺失后肽链暴露的表位, 从而能直接检测CDT的绝对水平, 但需同时检测血清转铁蛋白总量才能计算CDT百分比结果。HPLC和毛细管电泳法主要是将各亚型分离后再进行吸光度检测, 依据峰面积来计算出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百分比。HPLC和毛细管电泳法依据不用转铁蛋白亚型电荷差异进行区分, 可提供可见的转铁蛋白亚型条带, 并对不同亚型分别进行定量。虽两者条带图形相似, 但CDT检测的原理则不同。HPLC检测460470 nm处铁-转铁蛋白复合物的吸收峰, 而毛细管电泳法则是检测在200 nm处肽键的紫外(UV)吸收峰, 因而特异性不如HPLC, 而且无法排除电泳迁移率相同物质的干扰。而HPLC以其良好的分析敏感性、固有的抗干扰能力因而最终被WG-CDT工作组选为候选参考方法。
候选参考物质是选择何种转铁蛋白亚型呢?在2007年WG-CDT发表的第1份报告[29]时就指出将候选参考物质选为双唾液酸转铁蛋白。因为这一亚型是目前不同方法检测最主要的亚型, 而且与无唾液酸亚型相比, 这种亚型对慢性中度饮酒状态有更好的检测敏感性, 因而被选为了候选参考物质。为了屏蔽转铁蛋白水平变化导致CDT水平偏高或偏低, 结果以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百分比表示。随着CDT标准化工作的不断推进, 参考实验室从2007至2010年间进行了5次比对。候选参考物质有常温血清和干冰状血清物质, 双唾液酸转铁蛋白水平近2.4%。同时检测的还有一些CDT高值血清标本、严重嗜酒者的血清标本。从标准化检测的结果来看, CDT低值结果检测的变异系数(CV)最大, CDT高值结果的CV最小, 且各水平CDT的CV在不断改善。双唾液酸转铁蛋白水平为1.7%处, CV已< 5%。这也说明目前参考实验室已经具备了为参考物质定值的检测能力, 即在参考范围上限处, 双唾液酸转铁蛋白的不确定度可< 0.1%。
WG-CDT致力于建立CDT的参考检测系统, 包括检测方法、检测物质、结果报告方式。将参考系统对定标品和质控品进行定值, 从而使不同方法结果间具有良好的可比性。目前全球已建立了运用HPLC检测的实验室网络, 他们的CDT结果已显现出良好的重现性, 也已具备了对定标品和质控品定值的技术基础。候选参考物质本身也表现出了良好的稳定性。一套完整的CDT参考系统已初具雏形, 接下来工作组的工作将集中在制备一级参考物质, 并可能将目前以百分比形式表示的CDT结果转换为SI单位, 更好地发挥CDT在临床和司法领域的应用价值。
目前有足够证据证明影响CDT水平的因素包括饮酒、转铁蛋白基因突变、性别、终末期肝病等。而其他因素如慢性炎症疾病、体重、体液总量和药物等对于CDT的影响尚未定论。也曾有报道称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有免疫方法检测的假阳性结果, 但机制未明。
1.基因突变人类转铁蛋白有3种基因型, 分别是C、B和D。C型等位基因是最为常见的基因型, 占有绝对优势, BC或CD等位基因表达的转铁蛋白可能会干扰CDT检测, 分别造成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D基因型在白人中的发生率很低, 少于1%。但在亚洲人和南美人中发生率略高, 尤其是非洲人群发生率可达10%。而B基因型尤为罕见。目前已发现8种D基因突变类型, 这些转铁蛋白可能是由于糖链结合位点的氨基酸发生突变, 因而造成整条糖链的缺失, 使pI增高。在电泳检测中与CDT的电泳迁移率相同, 因而可能造成CDT假阳性结果。而B基因型转铁蛋白pI降低, 因而可能造成CDT假阴性结果。Helander等[26]对于1 614位研究对象的试验中发现BC和CD杂合基因在白人中的出现率分别为0.7%和0.2%。有研究证实在白人中因基因突变导致CDT假阳性结果的概率为1%, 但其他人群的情况还未知。目前也没有大规模的不同人群间流行病学研究来了解转铁蛋白突变造成假阳性结果的概率。但有很多试验证据已经足够表明在判断CDT结果时应考虑突变对检测的干扰影响。运用HPLC和毛细管电泳法根据不同转铁蛋白亚型的条带可判断出存在基因突变, 但目前还无法去除基因突变的干扰, 因而检测结果只能判断为不可信。另一种因基因突变而造成的检测干扰是CDG综合征。CDG综合征是一组常染色体隐性疾病, 发病率< 1/1 000人。患者有先天性血浆蛋白糖代谢障碍, 其血液中可有近一半的转铁蛋白缺失1条或2条糖链, 而血液中半乳糖和唾液酸水平增高。CDG综合征主要有4种类型, 大部分患者在儿童时期病情就可被诊断, 长伴有癫痫、精神障碍、肝损伤和心脏疾病等。CDG综合征患者CDT各亚型的水平均有所升高, 有些患者的CDT水平甚至可升高近50%, 仅有不到2.6%的患者CDT水平正常[30]。
2.性别CDT受到某些可升高转铁蛋白水平的生理因素的影响, 如铁缺乏、妊娠和女性激素等。以前使用的试剂因直接以绝对值表达结果, 因而尤其受到了转铁蛋白水平的影响。而FDA批准的试剂是以CDT和转铁蛋白百分比来表达结果, 很好地规避了转铁蛋白水平的影响。但目前仍有文献指出, 一些假阳性结果仍可发生于女性糖尿病或高血压患者[31]。有文献表明, 男性和女性在饮酒后水平升高的亚型是不同的。对男性而言, 饮酒主要使无唾液酸和双唾液酸亚型水平升高; 而女性升高的是无唾液酸和单唾液酸亚型[32]。此外转铁蛋白本身受类固醇激素的调控, 事实上转铁蛋白亚型的变化也受到了女性激素的影响。如女性在妊娠过程中CDT水平逐渐升高, 按每3个月进行检测, 结果依次为17.1单位/L、16.4单位/L和19.4单位/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1]。此外口服避孕药和激素替代治疗也会使CDT水平分别升高7.5%和45%[32]。而绝经女性的CDT比绝经前女性结果低近10%。虽然这些因素可通过将CDT与转铁蛋白总量的比值来得以改善, 但毕竟无法完全有效去除, 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CDT对于女性饮酒者的敏感性。女性出现CDT假阴性的情况也多于男性, 有几项研究发现饮酒过度的女性其CDT结果却为阴性[33, 34, 35]。有学者也推测对女性而言, 饮酒的方式对于CDT水平是否升高有很大影响。女性每天饮酒的次数比每天饮酒的量对于CDT有着更大的影响[36]。铁和转铁蛋白之间的平衡也会影响CDT水平[30]。作为主要的铁结合转运蛋白, 转铁蛋白在机体铁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也曾提出过疑问, 是否血清CDT与铁之间存在相关性?但结论也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认为女性血清铁与CDT间没有相关性, 但也有研究表示当机体铁过多时会降低CDT水平(饮酒者降低26%, 禁酒者降低39%), 而机体缺铁时会增加79%CDT水平。甚至缺铁性贫血患者在得到铁剂治疗后, CDT水平也有所下降。
3.肝脏疾病与GGT不同, 无论是CDT绝对水平还是CDT与转铁蛋白的百分比结果均不受急性病毒肝炎的干扰。但有确切的证据表明, 约有40%的严重肝病终末期患者的CDT水平会有所升高[30]。其中具体的机制不明, 但可能是与转铁蛋白水平变化以及糖化的速度有关。此外由于肝脏疾病也会导致蛋白糖化的异常[37, 38], 这可能因肝脏疾病的病理学原因所决定的[39]。因此建议转铁蛋白特殊的糖化形式(如双唾液酸-三唾液酸桥)存在时除了考虑转铁蛋白突变外, 还应考虑肝脏疾病的原因。
4.胰腺和肾脏移植在对于胰腺合并肾脏移植患者的研究中发现一半以上的患者CDT和CDT百分比结果都增高, 其中明确的机制未明。有学者认为血清CDT水平与胰岛素介导的糖摄取存在正相关性[40]; CDT水平升高与胰岛素敏感性增高也相关[41]。有趣的是, 胰腺和肾脏移植对于胰岛素代谢是抑制的, 对胰岛素有正面作用的同时也会提高CDT水平。
CDT作为评价饮酒状态的标志物, 具有较为理想的特异性。尤其是相对于其他肝脏酶类标志物, CDT在肝脏疾病存在时对于酒精摄入表现出更好的特异性和抗干扰能力, 更优于其他传统饮酒标志物且特异性更佳。随着检测方法学的不断发展, CDT在检测敏感性方面也得到不断改进。这些都促进了CDT向着更广泛的应用领域推进。但在临床和司法领域应用的同时, 不免还有较多问题需要解决, 如检测标准化的确立、单位方式的统一、不同方法间的可比性、转铁蛋白突变的辨别、某些肝脏疾病的干扰等。另外CDT与少量或中度饮酒、短期或长期饮酒间的效应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相信这些问题解决后, CDT将是个非常理想、可靠的饮酒标志物, 能为临床或司法部门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21] |
|
| [22] |
|
| [23] |
|
| [24] |
|
| [25] |
|
| [26] |
|
| [27] |
|
| [28] |
|
| [29] |
|
| [30] |
|
| [31] |
|
| [32] |
|
| [33] |
|
| [34] |
|
| [35] |
|
| [36] |
|
| [37] |
|
| [38] |
|
| [39] |
|
| [40] |
|
| [41] |
|